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艺术学理论前沿系列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主办。《从文化艺术上,如何言说我们的时代?》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李心峰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晓霞主持。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晓霞 主持
孙晓霞从学术视角对李心峰老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李心峰于1988年发表了《艺术学的构想》 ,从学理层面首次阐明了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此后,李心峰陆续出版了《元艺术学》《现代艺术学导论》以及《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等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艺术学的理论内涵与学科脉络,是艺术学界理解和掌握20世纪中国艺术学科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
在学术探索中,李心峰不断提出新理论。继“元艺术学”理论之后又对“通律论”进行了新的阐释。2023年,其著作《日本四大美学家》荣获“啄木鸟杯”著作奖。与此同时,李心峰带领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当代艺术学史的研究。自2011年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起,团队便着手编撰年度艺术学科发展报告,至今已持续十四年,每年均有系列专题成果问世并被收录于各类年鉴。这种看似基础却极具累积价值的工作,让我们得以见证学科在十余年间的演变,意义非凡。基于此,2018年李心峰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并于2023年以“优秀”等级结项。
孙晓霞指出,李心峰的学术探索犹如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思考学术问题,其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其根基向深处扎根,枝叶向广处伸展,不断突破自我,为我国艺术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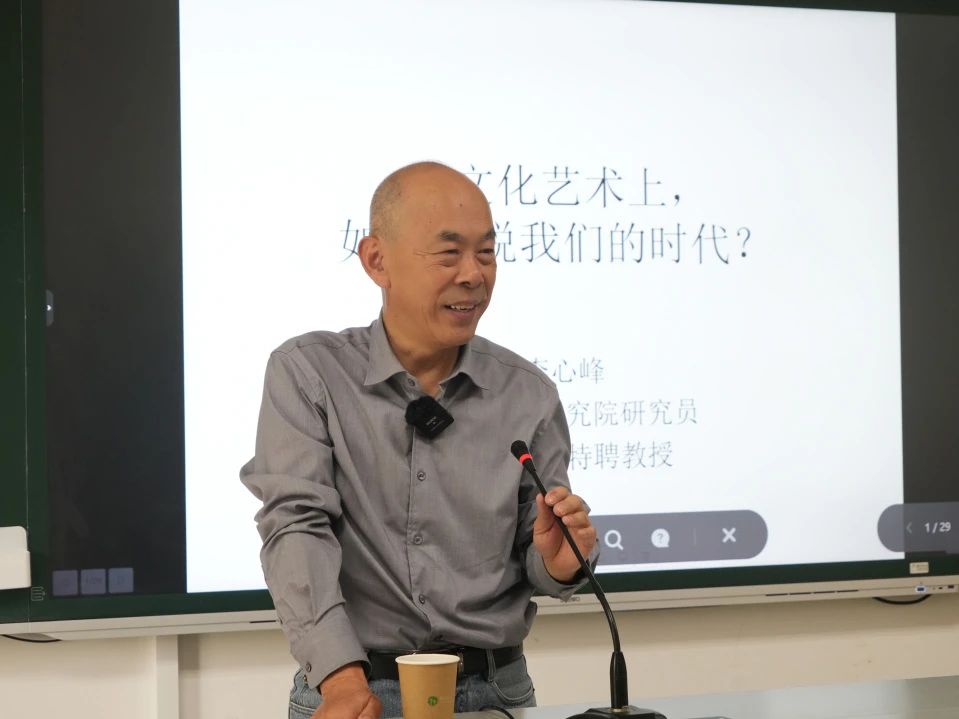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李心峰
课程内容回顾:
《从文化艺术上,如何言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立场来给我们的时代命名?李心峰从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引出话题,回顾了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探讨二者关系对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至关重要性,并讨论了如何从文化艺术层面言说、命名我们的时代。
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艺术理论的重大课题
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是艺术理论当中一个基础且重要的课题。作为艺术的基础理论它会关注很多问题,如艺术是什么?艺术的功能、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发展规律等,还有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民族,艺术与人民等都是艺术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像艺术与民族,艺术与人民、艺术与国家这些问题大家思考的比较多,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艺术与时代。我们需要将艺术与时代的一般原理运用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为艺术提供了什么,二是艺术为时代提供了什么。通过抓住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这一切入点,更好地展开思考。
回顾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我们会发现许多名家常常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更是将这一关系置于重要位置,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剖析。在当下的新时代,对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又赋予了更具时代特色的系统性论述。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时代的发展也需要艺术的滋养。因此,探讨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不仅是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对于一定的时代,在文化上如何言说
对于特定时代的命名,尤其是借鉴“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文化艺术的特定阶段,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在中国,不同学者将不同历史时期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繁荣,以及唐宋的文化变革等。然而,这些命名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原因在于“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被变革,其与西方13至16世纪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而中国的文化历史情境与之存在显著差异。
“文艺复兴”在西方语境中,既是对古代文化的再生,又强调变革、创新与创造,同时与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条件下形成,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将其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历史时期,往往显得“水土不服”。
我们是否应以西方“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来命名和言说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许多非西欧国家尝试借助“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来表征一定的时代。美国学者曾以《美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出版著作,试图运用西方文艺复兴的概念来评判美国某一定时期的文化艺术状况。这种言说虽有其特定内涵,却未成为美国的主流话语。
东方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如日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言说,尝试用“文艺复兴”或“文化再生”等概念来描述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如菲诺洛萨、冈仓天心。在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是否有类似“文艺复兴”言说的出现,有待进一步挖掘。
关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称做“文艺复兴”话语的世界旅行。
回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自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的艺术界在《讲话》精神引领下所进行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实践、艺术的理论批评实践,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实践的一部分。中国今天的艺术发展状况如何?中国当下的艺术理论批评发展状况如何?便成为艺术领域需要我们观察、分析、概括、判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艺术领域需要我们勉力回答的“四问”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面对新时代,我们如何言说?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我们面临着如何言说自身所处时代的课题。这不仅是对时代特征的描述,更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深刻反思与表达。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凸显与强调,这体现在坚定文化自信、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及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因此,我们不仅要对时代进行命名,更要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此来延伸和深化我们对时代的理解。
这种文化自觉和自信,要求我们真正站在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上,去探讨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我们需要从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需求出发,构建一套能够准确反映新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
2024年艺理会年会以“时代之变与艺术之变”为主题,这一主题讨论了时代变化与艺术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数字化时代,艺术的变革尤为突出,成为当下艺术变化中最为突出和前沿的现象。
理论与批评上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
我们立足于中国新时代以来的艺术理论批评的实践,从我们的现实实际情况出发,在历史的脉络中,在世界的视野下,在与其他国家、区域的对比中,将中国新时代以来尤其是《讲话》发表以来的艺术理论批评的总体状况,予以宏观总体的概括,为其命名,是我们对于今日我国艺术领域所发出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的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尝试性的回答。
在中国新时代的语境中,我们将其称为“中国艺术批评的时代”。所谓“批评的时代”,是文学批评、艺术批评领域的命题,专指人们对于一定历史时段文学、艺术批评状况的总体的观察、概括。当然,也有人在其他如哲学领域使用“批评的代”的命题,将康德的三个批判哲学著作的问世,看作“批评的时代”到来的标识。这是将康德的"批判”与一般所说的“批评”等同起来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批评的时代”,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
讨论“批评的时代”这一命题,还需要把它放在世界的视野和历史的脉络之中予以解析。所谓“批评的时代”,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实践中被人再三讨论的话题。其含义大体上是指在一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文学批评、艺术批评高度繁盛,形成一个不同凡响的高峰,也可以说迎来一个批评的黄金时期。人们往往将这样的时期称之为“批评的时代”。
在世界批评史上比较早地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批评的时代”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他在其仅有37年的短暂生涯中,留下了多达十三卷的文学与哲学等著述。仅仅精选了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精华而并未包括其著作之全部的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便有六大卷之巨、300余万字。
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自1952年出版两卷本到2006年推出最后一卷第六卷,历时长达半个多世纪,满涛与辛未艾二位著名俄语翻译家为这套选集的翻译、出版耗尽毕生心血。当第六卷面世时,二位译者均已作古,未能看到六卷本的全部出饭。在辛未艾翻泽初稿基础上将第五卷、第六卷尚未做完的校订等工作承担下来,是由另一位翻译家冯春用数年时间倾力完成的。而且他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冠心病发作,让他的校订工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被迫中断。因此,六卷本《别林斯基选集》可以说“是译校者倾注了生命的呕心沥血之作”。他们几位译者的艰辛付出,为我们留下了世界文学批评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四十年代初,他针对当时一位彼得堡大学教授《关于批评的讲话》单行本写了一组书评。《关于批评的讲话》,是当时俄国国立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亚·尼基简科1842年3月25日在该大学庆祝大会上所做的演讲,后于是年出版单行本。别林斯基针对这部小册子写了三篇论文(书评)。在第一篇书评中,别林斯基十分自信地将他从事文学批评最活跃、最有成就也最具影响力的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在他关于他的时代的分析、讨论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时代(主要是进行思索和判断,因而是进行批评的时代)”。得出这样的观察、思考、判断,主要的依据是,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时代氛围,一切都要拿来在理性面前重新加以审视。
别林斯基指出:“我们的时代,整个儿是问题,整个儿是追求,整个儿是对于真理的探索和向往……”“现在,理性在一切事物里面都要寻找自己,只把包含有自己在内的东西认为是现实的。我们的时代就是以这一点来显著地区别于一切先前的历史时期的。理性使一切东西俯首听命于自己,凌驾于一切东西之上”。(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572-573页。)
还有一点,就是文学批评格外活跃,盛极一时。的确,这个时代,俄罗斯的文学批评,巨星辉耀,经典名篇纷纭繁多。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艺术批评活动最为活跃、成就最高的历史时期,堪称俄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巅峰时代。别林斯基将他那个时代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可谓实至名归。
在别林斯基之后,在世界批评史上更加明确地使用“批评的时代”来为一定的历史时期命名的,有美国二十世纪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威勒克。他在其代表作之一《批评的概念》一书中的最后一篇论文《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一开头就掷地有声地断言:“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威勒克:《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威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在他看来,在20世纪,“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相当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方法并得出了新的评价。甚至在19世纪后期,除了法国和英国,文学批评还不能超越地区的局限。今天在以前似乎处于批评思想的外围的一些国家中,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受到重视,这些国家有克罗齐以来的意大利、俄国、西班牙以及后起的但却不可忽视的美国。对20世纪文学批评想得到一个概观就必须看到这种地理上的扩展和同时发生的方法上的革命。”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批评的数量上的增长、批评的自觉程度、批评受到重视的程度、批评的新方法的不断涌现、批评影响力的扩大等方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为了论证20世纪更适合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威勒克在该文中概括了20世纪文学批评的“至少有六种主要新趋势”:(1)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2)心理分析的文学批评;(3)语言学和文体学的文学批评;(4)新的机体主义的形式主义;(5)以文化人类学所取得的成就和荣格的思想为基础的神话文学批评;(6)受存在主义及与其类似的世界观的启发而形成的新的哲学性质的文学批评。
“批评的时代”作为一个批评学、批评史话语,主要是从理论史批评史的视野对一定时期批评状况所做出的历史性的判断。即将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学艺术批评放置于它所处身其中的一个更为宽广悠长的历史时段中,观察该特定历史时段的批评,是否与其他历史时段有显著的差异,是否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成就与超乎寻常的辐射力、影响力。如果确实能够得出肯定性的判断,对于这样的时代,就可以把它叫做批评的时代。
“批评的时代”已经成为世界批评史的“公共话语”。自西学东渐以降,中西文化交融互鉴,促使中国批评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当下,批评活动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态势,甚至可被视作黄金时代或高峰时代。对理论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在体制机制上得到了充分保障,还在观念意识层面得到了显著提升。评论家与理论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成为艺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过去十年间,批评的总量无疑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同时,优秀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不断涌现,批评的样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批评的时代”。
创作上如何言说新时代——外国艺术史的案例
约1760-1780年代,德国出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代表作品包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席勒的《强盗》。这一名称源自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1776年的作品《狂飙突进》。
“印象主义”源于1874年莫奈的《印象·日出》参展。评论家路易·勒鲁瓦(Louis Leroy)在批评性报纸《喧噪》发表《印象派展览》首次使用“印象派”(印象主义)一词。虽是出于讽刺,却被这批属于未来的青年画家欣然接受。
在讲座的尾声,李心峰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既有的、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经典作品中找到合适的名称,来言说乃至命名新时代的艺术?我们又该如何从创作的角度去言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整个艺术系统甚至整个文化层面,又该如何进行言说与命名?这些问题,仍待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孙晓霞总结:
孙晓霞在总结中指出,李心峰的讲座视野宏阔,问题意识鲜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尤其在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感受到挑战。李心峰从文化角度探讨了我们的时代性,尤其是他对文艺复兴的讨论,引发了我对“文艺复兴”概念的思考。研究艺术学史可知,“文艺复兴”最早由瓦萨里在16世纪塑造而成,他试图将古代与16世纪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这一概念的理论化是在19世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实现的,其中全面地将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礼仪等生活细节与古典文明联系起来,强化并专业化了“文艺复兴”概念。而现在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已成为历史的专属名词,通过历史与理论的建构,西方人重塑了自我形象。19世纪的学者通过书写再造历史,让西方成为西方,让欧洲成为欧洲。这种自我历史与理论的建构,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今天的人文学者,处身于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应如何对自我进行学术身份的设定?我想这是这场讲座给在座各位同学提出的问题。
同时,李心峰对问题的敏感性和理论的开拓性驱动着他试图为这个时代命名,从理论上这是对艺术的知识体系进行扩展和延伸,而从思想上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精神之体现。他鼓励我们思考中国的艺术与文化如何定位,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与全球艺术对话,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提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艺术史的模仿和复制上,而应该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内核,寻找与新时代的契合点。言说新时代,李心峰的讲座命题宏大,但实际关切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学术成长道路与未来方向。这是李心峰讲座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