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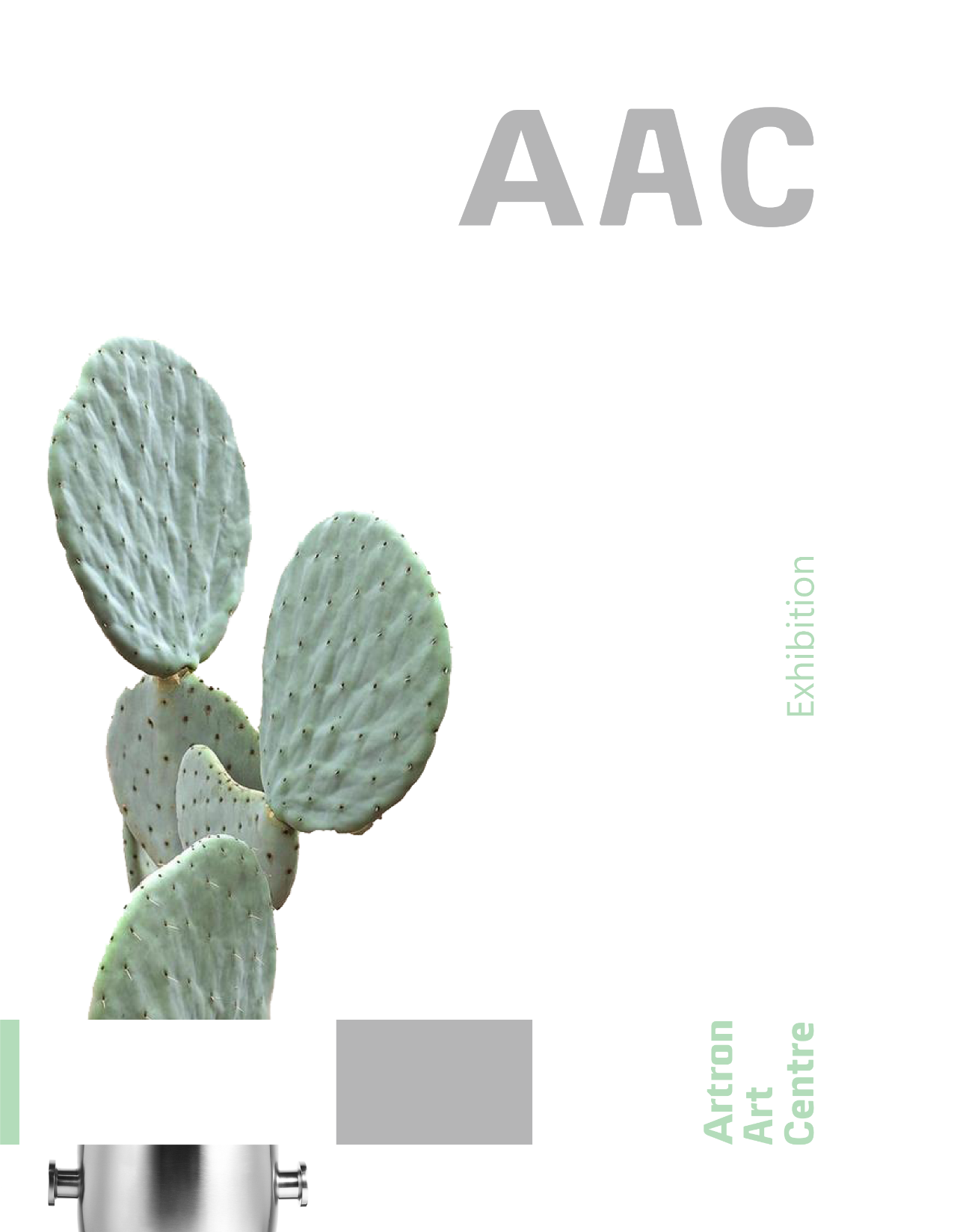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从网络上知道了艺术家尹秀珍,不过那时候对于她在当代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不甚了了,对艺术家本人及其在艺术界的名气也一无所知。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时内心引发的触动,这种触动伴随着作品的图式印象被深刻地留存在记忆里!
其实那种触动并非视觉或者心理上的被震撼,只是一种透过网络图片也能察觉到的艺术穿透力,推敲起来,亦即作品形式上的独创性,这种形式进一步引发了观者情感上的深层共鸣,因而具有强大的艺术表达力量。这样一位女艺术家,作品传递出来的强大的情感力量会让你去联想到那些站在艺术金字塔尖的女艺术家们,诸如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日本女艺术家小野洋子或者南斯拉夫女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会去猜测一个顶级艺术家背后的故事与处世的风格。但是当你真正面对尹秀珍本人才会发现,她跟她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相反,她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女艺术家,谦逊而低调,同时带有强烈的中国当代史印记——这一切跟时尚无关,跟热烈奔放的个性无关,似乎也跟激进的艺术野心无关。她的作品具有非凡表现力,如果深入地去了解尹秀珍,你会发现她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远比她已经拥有的显赫的名声走得更远!

尹秀珍
Yin Xiuzhen
1963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现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尹秀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了她的当代艺术实践,她的作品具有实验性和多样性,把不同人的经历、记忆和时代的印痕作为创作的元素之一,并对材料进行反思和实验进行了大量的不同形态的艺术创作。作品涉及装置、行为、陶瓷、影像、绘画雕塑等众多领域。

尹秀珍作品《武器》
我最初所见的尹秀珍作品是一件名为《武器》的装置,即便已然如此令人印象深刻,这件作品却并不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如果以一个艺术理论家的视角来看,“代表作”这样的词汇暗示着某些世俗的成功学偏见,实际上每一件作品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如同电影《喜剧之王》的台词:“没有小角色”,这也是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言。每一件艺术品都传递着艺术家情感的表达,尹秀珍的作品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身边每一个人的生命与灵魂的印记,当然,也包括她自身,这就是她的艺术如此触动人心的原因。维特根斯坦说过:可以言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言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当代艺术是一个混杂了哲学、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概念的综合体,是一个抽象且形而上的理念,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精确地论述清楚的,但艺术作品是具体的,艺术本身就是另一种语言,作品即是表达!符号化的艺术语言是需要解读的,因此,以成功学意义上的眼光去审视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是唐突且鲁莽的。艺术语言依附于艺术家而存在,而艺术家是十分具体的,倘若从艺术家出发对艺术作品进行关照则至少能找到一个最为重要的审量当代艺术作品的参照系——没错,仅仅只是参照系!因为当代艺术作品所能够引起的思考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观众在面对一件当代艺术作品的时候,内心所引起的共鸣、思考或者情感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再创造。而这种杂糅了艺术家身份政治、艺术语言、展览环境与观众心理的混合体正是当代艺术所传递的价值意义所在。
当代艺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在具体的艺术家身上则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色彩。虽然这对于纯粹专注于艺术表达的艺术家而言很多时候是不屑一顾的,但套用黑格尔的话说:艺术是艺术家的感性显现。艺术家尹秀珍在当代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一切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对于大多数当代艺术家而言,进入顶级藏家视野、在顶级画廊或美术馆举办个展以及被举足轻重的理论家和策展人认可基本上意味着艺术终极梦想的实现,然而,生涯巅峰很可能意味着终点,因为理想一旦照进现实,剩下的就只有俗世。但对于尹秀珍而言,即便她已经在诸如佩斯画廊、格罗宁根博物馆、杜塞尔多夫美术馆等当今艺术界最重要的一些艺术机构成功举办过个展,一个阶段的终结却往往是最好的开始,一如当前正在佩斯北京画廊展出的个展主题——“以终为始”,如果观照艺术家的艺术履历,会发现其整个艺术生涯都在不断地周而复始,在近乎毁灭的不安中带有某种诗意地重生。一切还要从故事的开头说起。
对于艺术家尹秀珍而言,“以终为始”似乎就是一种人生经验的轮回!
1
落榜为终,绘画为始
尹秀珍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在建筑队,因为工作关系,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京棉二厂下边的服装厂工人,一个人养着四个孩子,十分辛苦。京棉二厂也就是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原址位于北京东八里庄,今天的东四环外,在当年可算是绝对的郊区。尹秀珍一家住在工厂宿舍里,童年的记忆大多跟服装厂有关。棉纺织厂的记忆是尹秀珍日后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跟日常生活切身相关的衣物早早便根植于潜意识深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为未来铺垫着,只是当时而言,尹秀珍丝毫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更不知道艺术家会回到记忆的开始找到那些诗性。
尹秀珍在家里排行老三,个儿却是最“袖珍”的。尹秀珍后来回忆说,自己不长个也许跟跳芭蕾有关,那时候看电视上跳芭蕾,自己就在家踮着脚尖学,上下楼梯都踮着脚尖走,也在屋子里练习各种劈叉,横劈、竖劈练得十分起劲。也许是练习劈叉抻着筋了,影响了长个儿,后来连妹妹都长得比自己高了,以至于很多活儿母亲甚至吩咐妹妹去干,以便照顾小个儿的尹秀珍。这或许反倒给了尹秀珍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画画儿。不过走上绘画的道路,主要是受姐姐影响。姐姐很喜欢画画,但初中毕业后插队下乡去了,没有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少年尹秀珍曾跟随母亲一起去探望插队的姐姐,在那儿看到了很多姐姐画的画儿,这让年幼的尹秀珍兴趣盎然,回到家之后就开始自己动手画画儿。
那时候的尹秀珍可并不知道当画家这回事,只是基于纯粹的兴趣。后来姐姐知道了尹秀珍喜欢画画的事,便给妹妹买了纸、笔和颜料,也买了一些诸如“文艺复兴三杰”的绘画图书,便于临摹和学习。稍长之后,姐姐工作调动进了工厂宣传科,尹秀珍在姐姐的影响下开始画一些工农兵人物形象。不过,即便如此,尹秀珍依然没有往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的契机是因为高考落榜。当时的尹秀珍其实学习十分刻苦,不过那会恢复高考不久,竞争十分激烈,尹秀珍最终落榜了,没能进入大学。之后,尹秀珍一度找不到方向,曾跟随做建筑的父亲学习给门窗刷油漆,毕竟那也是一条生计。偶然的机会,尹秀珍了解到了中央美术学院有绘画培训班,进入了培训班之后才发现,原来学画画也是可以考大学的,并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由此踏上了成为艺术家的第一步。
2
公职为终,画家为始
大学毕业之后,尹秀珍并没有立即成为画家,毕竟当年并没有职业艺术家的概念,少数的自由艺术家经常被当做社会不安定分子的盲流被四处驱逐。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尹秀珍工作分配成为了工艺美院附中的老师。尽管在这份工作上坚持了十年之久,在当年也是具有稳定收入的铁饭碗,但是这始终无法燃起内心的激情,并且,自己的教学理念跟现实状况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
当时,尹秀珍已经开始参加一些外界的艺术展览或者相关的活动,因此不得不经常向学校请假。而在教学课堂中,尹秀珍经常会跟学生们讲一些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也会用幻灯片的方式将一些当代艺术作品和相关艺术活动播放给学生观看,让他们了解到艺术并非只是画画,当代艺术与以往相比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观念转变。不过这并非校方所希望看到的,一直以来,应试教育是中国所有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这种教育体制是无法打破的,学生、家长、学校以及整个体制严密牵制的利益关系也不容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尹秀珍的教学显然打破了这种平衡,校长不得不找她谈话,要求她权衡厉害关系,不要过于激进,毕竟学生还是要考学的,这些内容待大学之后再了解不晚。但对于尹秀珍而言,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如果不适时地给予学生以新观念的输入,日后难免形成定势而无法挽回。基于教学理念与校方要求的格格不入,同时,自己也在当代艺术领域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也在寻找一些机会,尹秀珍最终放弃了旁人称羡的教师公职,开始寻找自己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未来。
3
写实为终,当代为始
辞职之后,尹秀珍很快作为基金会受邀驻留艺术家去了德国的一个小镇进行了为时一年的当代艺术学习和实践。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尹秀珍最终彻底脱胎换骨,明确了自己当代艺术探索的方向,并由此而走向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
这是一个叫Badems的德国小镇,基金会位于一栋俄罗斯人留下的大楼里,里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安排了起居室、工作室以及图书馆。因为基金会是公益的,尹秀珍得以毫无压力地释放了自己的艺术天性,同时也借机遍览了德国各地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最终尹秀珍彻底放弃了架上绘画的努力,开始专注于装置艺术的尝试和探索。这在当时的中国,装置艺术还是新事物,不被艺术界接受,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但很快,尹秀珍开始找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朋友,大家一起进行着当代艺术的尝试。
尹秀珍的尝试也得到了丈夫宋冬的支持,宋冬是自己的大学同班同学,因为艺术上的共同追求走到了一起,现在他们共同为了新艺术而彻底放弃了架上绘画。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4
毁灭为终,重生为始
2017年年底,尹秀珍在佩斯北京“以终为始”的个展开幕,在展览的入口处放置着作品《信息没有送到》,这是一个插满尾气管的水泥雕塑,一个坠毁的天使;《容器-时间》中,金属钟表在陶瓷板上留下了炸裂瞬间留下的“伤疤”,记录下了那个破坏的瞬间;《种植》是一片长在坚固冷酷的水泥中方阵中的杂草,在荒芜中枯萎的杂草显得毫无生命力;在最里边的巨大装置《木马》则是典型的尹秀珍式作品,一个用旧衣服制作的6米高巨型雕塑,这是一个坐在飞机座位上保持着双手抱膝防冲撞姿势的女性,似乎在等待这灾难的来临。一切都指向着毁灭,不过在毁灭中却似乎传递着另外一种诗意的温暖,比如充满危险性暗示的《木马》,如果进入到作品的内部,会发现身处其中的人们充满着温暖而炫目的安全感。但艺术家给这件作品名之以木马,却似乎指向了不同的隐喻,毕竟木马内部隐藏着的才是真正的危险,或许危险是来自自身。这也许便是展览“以终为始”的真正所指。
“以终为始”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用策展人的话来说,艺术家“以其感性而敏锐的创作直觉捕捉了当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主流氛围背后的迷失与不安”,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传递着一种末世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却将观众的遐想带入了一种宁静的趋势,那是一种重生之境。
显然,对于艺术家尹秀珍来说,所有的毁灭终将化为异日的诗意重生。

艺术家问答
Q:您是北京“土著”吗?童年在记忆中是什么印象?
A:不是,父母因工作才迁入北京。我在北京出生,跟宋冬结婚后才算城里人,因为他家在胡同里,我家那块不是。我妈在京棉二厂那,冥冥之中我还是没有逃出那个纺织厂,作品跟那有关系,有些作品布料也是那儿的,甚至后来租的库房也是原来厂里的。
Q:您是怎么走上学艺的道路的?
A:学艺受我姐影响,她比我大9岁,喜欢画画、剪纸、看书,但没教过我。她支持我画画,给我买纸、笔、颜料和书,有文艺复兴三杰画册,如《米开朗基罗》。这次开幕想找来着,没找到,后来发现被我哥锁在一个抽屉里,他说那上面有裸体,不能看。其实就是雕塑,哈哈。后来高考没考上,就成待业青年了。因为周边没有人学画,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有艺术类大学。但好多事都是偶然的,报美术班也是,看到电线杆上贴的美术班招生广告,就报了名。那会两块五学素描,五块钱学色彩,后来又涨成了十二块钱。报的第一个班是我们家那边的红领巾公园,还有什么朝阳文化馆以及崇文门那边的都去过。班挺多的,有时候报完了发现没意思,钱也不要了就走了,换别的班学去了。因为看他们画的石膏眼睛,我比那水平高。在班里画素描的时候发现,他们一聊天都说要考大学,什么艺术类大学、美院、戏剧学院之类。
Q:所以您后来就通过美术班的学习考上了首师大?
A:对,首师大也有班,我觉得考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的“学前班”。
Q:北京的艺术氛围一直都不错,您上大学的时候新潮美术就开始了,先后还有星星美展、现代艺术展等现代艺术史上的大事件发生,对您影响大吗?
A:对,那时候新潮美术在全国已经开始了,我老去美术馆去看展览,就像朝圣一样。当时还有劳申伯的展览,觉得那个怎么是艺术,怎么能这么做?因为你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背景,根本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过,突然看到有这么一个展览,冲击特别大。
Q: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件装置?
A:记得,记得,那是在朱金石家。他在九四年“后十一”那个展览的时候,把屋子给腾空了,几个艺术家在一起弄点东西,就是要逃离绘画,感觉就是玩那种,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装置艺术。我做了一个作品叫《关系》,用石头、茶叶、大米在他家地板上弄了两个人的形状。朱金石觉得太占地方了!他们家就十几平米,只好卸了一个厨房门,把两个人弄门上边了。那时候还老去户外做,因为没工作室,也没地方展览,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做点东西。
Q:现在全国艺术家都往北京跑,很多老乡们会聚在一起,因此产生了福建帮、川帮、湘军等,出生在北京有什么不一样?
A:北京艺术家?好像没有这概念。都在北京,都是北京艺术家。我不是那种混圈子的,我没圈子,没有经常性的跟谁聚在一起。最早接触的外地艺术家就朱发东,张洹,庄辉,那会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因为要租房子,吃饭。我和宋冬有工作,还不用交房租,有单位的房子。
Q:当时有哪些理论家在活跃?
A:那时候就是黄笃、冯博一、钱志坚、冷林,老栗。
Q:那时候参加展览应该也不是特别多?也没什么艺术市场吧?
A:不多,而且还没有卖过作品。其实挺早的时候就特别纯粹,根本没想过能卖作品,就跟当初不知道还有艺术类大学一样,特别单傻。宋冬那会也当老师,在四十一中,我们俩没有工作室,住的地儿就一个十平米的小屋,终日不见阳光。
Q:作品能销售应该是后来的事了吧?
A:应该是99年在德国学习之后,当时是庄辉帮的忙,他跟希克关系比较密切,就推荐希克买《衣箱》那个作品。庄辉还买了我那个照片的作品,他做摄影,比较早买作品,感觉他可有钱了,天天打车,我们哪舍得打车啊。哈哈。
Q:后来走向国际跟德国基金会的经历应该有很大关系?在德国的学习经历怎么样?
A:那会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都是外国人。中国因为没有地方展,老外能把作品弄到国外去展览。德国那个基金会在一个很小的小镇Badems,老年人居多,是个养老的地方。当时我们经常坐火车去法兰克福、科隆、波恩,包括柏林。柏林比较远,周末去柏林大概25马克,反正比较便宜,周末四个人买个家庭票,一凑钱就去了。当时大家都没钱,怎么省钱怎么来。
Q:你跟他们都是用英文交流吗?
A:这就比较奇怪了,都是用肢体语言。他们应该是会英文的,但是我英文很不好,德语根本就不会,所以在那的时候开始学英语,自己带一本电子词典,在图书馆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查完一个词下楼碰见人就跟人家说。
Q:所以你去德国学英语了!
A:对!所以我能听懂德国人说英语,对我来说他们的英语更容易懂。有一次一个美国人过来参观,他说话我听不懂,然后旁边的德国人帮我翻译,把我逗的。当时就年中和年底有两次展览,在那一个月规定不能离开多长时间。每个月有大约两千马克补助,差不多一万块钱,但如果考勤不够数就扣钱。当时觉得那些钱特别多,因为我辞职时还不到一千块钱工资,所以当时在德国就还省着花钱,想着回来不是没工作了吗,呵呵!不过那边消费也高。感触挺多的,生活上一些,艺术上一些,还有就是工作态度。那一年收获特别多,包括做饭我也可以了。
Q:原来自己不做饭吗?
A:原来不会,都是宋冬做,我给他做助手。洗菜、买菜、切菜、刷碗,其实我干活干挺多的,但人家是技术活,哈哈哈。
Q:宋老师掌握了核心技术,哈哈。是从那时候开始跟国外联系开始多了起来吗?
A:其实我是不善于跟外界联系的人,我特别懒,写信什么的,一封信写半天。英文的写不好,我特怕写英文,特别麻烦。
Q:我感觉这段经历对你挺重要的。
A:影响非常大,就那段时间看东西、学东西,自己学英文,E-mail是在那学会的。
Q:那你申请不是自己申请的吗?
A:别人帮我申请的,哈哈哈,所以人家以为我英文挺好的,结果到了那就会那点。
Q: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近年来十分炙手可热,会对自己的市场行情关注吗?
A:其实你的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是不是成正比我不太关注,我是能活着就行了,要求不是太高。你看我这大衣其实就10块钱,后边有一个洞,我就补了起来,其实也挺好。围巾也是摊上看的,也是10块钱。我比较随便,没有特别的要穿的什么牌子。但我觉得个性挺重要。其实艺术都是先做给自己看,然后才是别的,而不是说为别人而活的。就这样。
Q:有没有觉得贫穷艺术对自己影响比较大?
A:没有,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最早做装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叫装置。
Q:艺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A: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还有感觉,你是一个人,对它还保有感觉,而不是麻木的。
Q:感谢!
展览时间持续至10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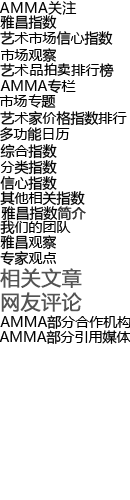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