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社会语境下的艺术家个人表达
分享会主持人:米诺
特邀嘉宾:夏可君 段少锋 朱赫
时间:2022.10.15 PM 15:30
地址:Morning Art & LiZi Studio(北京顺义区裕民大街3号院北京方糖1单元907)
米诺:今天是在栗子的工作室,讨论艺术家栗子的作品《160分贝》,同时这也是一个项目展览,源自我发起的一个新的项目--《正在发声》,《160分贝》正是这个项目里的一件作品。今天邀请了三位策展人夏可君、段少峰和朱赫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栗子的这件作品。
为什么要做这个《正在发声》这个项目,主要还是跟疫情有关系,我们现在处在疫情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最多的聊天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延期或者取消,刚才我跟段少锋聊天,他上半年所有做过的展览都挤在下半年了,当时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发起这个项目,也许就是觉得因为太多的被取消、被延期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及时发声,及时表达的一个出口。
栗子的这件作品呢,其实是两年半以前就做了,时间是2020年,当时大家都知道武汉发生的事情,当时栗子在武汉被困了四个多月,她是完全的经历了整个武汉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栗子这件作品,是一件装置跟影像结合的作品,这件作品在一张床上展开,床上面有一匹狼,也有几十部手机,这个手机里面的视频内容一部分是她当时自己记录的,也有一部分是从网上下载的,也就是传播量比较广的这些视频的内容。栗子经历了当时武汉的这个疫情,《160分贝》表明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通过这种声音冲出武汉,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但是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正在发声》里面,就是因为她的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明知不可为,就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今天分享会的主题叫“社会语境下的艺术家的个人表达”,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限制语境下的个人表达,当然这个限制没有更多的歧义,但是很多时候大家是了解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她这些作品展出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要做这件作品,我们可以先请栗子来讲一讲这件作品。

(从左往右)朱赫、栗子、米诺、夏可君、段少锋
栗子:当时是2019年12月10几号,在我去武汉之前,武汉那边就开始流传有一种感冒很严重,类似非典一样,当时家人说不要回去,但紧接着当地就辟谣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被困在了武汉。从被困在武汉到可以来北京,我见证了整个的过程。
当时在武汉被困在家里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有很多人感染,虽然和家人在一起,当然也有物资,不至于到没有东西吃的那个阶段,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恐惧和愤怒,人变得特别容易暴躁,因为你被关起来了,被关在一个你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再也出不去了。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明星索菲娅罗兰演的,那部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演的是那个火车上有一群人,他们得了一个病毒在乘客之间传播开了,然后政府就让他们上一座危桥,上这个桥的时候,这辆火车就肯定会掉下来,那这个病毒就死在车厢里,就不会再往外面传播蔓延。当时我就一种很恐惧的感觉,情绪也非常非常的恐慌,我想完了,因为你会觉得死亡离你特别近,你甚至会觉得像卡桑德拉大桥那种状况,就是会为了让整个世界变得很干净,然后整个城市的人都会死掉,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你不知道这个病毒在哪里,因为它也看不见也摸不到,小区里每天都会有人生病,也有死去的,你不知道他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然后我们只能把窗户开这么一点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就是在这样的恐慌中,慢慢的过去了,当时我心想,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品,要把这个恐怖的情绪,还有这种极度的恐慌表达出来。当时拍到从我家窗外看到的一些景况的视频,比如没有人的街道,我想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品,我们不能去宣扬这种负面的情绪,但这种负面的情绪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你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宣泄出来呢?所以我做了“160分贝”这个作品。
因此为什么这个作品叫《160分贝》,“160分贝”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声音,这是非常有穿透力的声音。当你发出160分贝声音的时候,其实这个发出声音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消失了,就像水一样化掉,就化成一堆血水,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发出这个声音?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发出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了什么含义,我们无法说得太多,就交给别人去说吧。

《160分贝》
米诺:刚才栗子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积压,但其实她也有很正面的东西,我觉得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了这个《正在发声》,事实上这个作品已经是一个完整式的,但我们今天想讨论的是艺术家的勇气,真的是这样,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件作品呢?我觉得栗子甚至都没有考虑到展出,但她为什么要做,我觉得可能是情绪的一个激发点促使她要来一定要把这个作品实现。
夏可君:就栗子的这件作品而言,因为2020年的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生和死,在过往年代,在和平年代,无论2020年带来一个不再是过往和平的安宁的年代,到了今年俄国战争以后都没有和平了,从一个2019年以前的一个充满着冷战以来的难得的一个人类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安宁和平的年代,我们进入一个生死的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想作为一个2020年在武汉的现场的艺术家,栗子就提供一个个案,这个作品作为一个已经消逝的,现在武汉都已经和有点祥和了,比如说以前、在020年的元月到五月,武汉的那个紧张的惊恐的气氛,其实是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可能说武汉人连健忘的中国人可能都容易忘记。
可是这个作品,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包括今天看还是让我有种震惊,震惊在什么地方呢?我就简单分享这个作品它本身的构成。第一个对象它是一张床,一张白色的床,那这个白色床象征是我们出生一张床上,我们死于一张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张床是一个孤零零的床,他象征就是说我们关闭在一个房间里,最后死的时候我们的旁边没有人,就像一个孤独的人在那床上悄无声息的。第三个,这个床上他是个舞台,是一个静止的、被缩小了一个舞台,这个白色的床是这些象征,当然女士比较喜欢用床的作品,比如泰特那个女艺术家获奖就一张床的作品,我想女人可能比男人对床更敏感,这是床的一个分析。
第二个对象就是那只狼,栗子在在机场里面看到了狼,因为疫情这个病毒带给人类的教训是这样的,就是人类过度的伤害环境,就是它的对生态地理环境的破坏上面,人类实在冒犯武汉,在别的城市没有,因为武汉太大,武汉的水又这么多,所以你导致后果就更严重,比这干旱的地方,那水是自然,我认为这种自然不是比人低一级的自然,我认为是一个神圣性的自然。这个病毒就把一个人在大路上就把人击倒了,可是病毒活得好好的,这个病毒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与人类同行,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病毒面前啥都不是,自然是神圣的,人是有限的,所以这是这个自然告诉人类,我的力量比你强大,你别以为想把我干倒。那么狼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显现,就是对于栗子看来这个狼当然是孤独的狼,动物生是一种自然的显现,一种自然的化身,当然这只狼在栗子这里还不只是一个所谓的自然的神圣性的显现,它还是一个什么呢?惊恐,因为狼是让我们感到恐惧,狼是吃人的,我想在武汉的那段时间里,武汉人是最能够比我们在外面的人感受到的恐惧,因为在医院里大量的人倒下去,所以这个惊恐只有在现场里面才能经历得到。
第三个是手机视频的图像集合或蒙太奇组合,如果只是一张图片,少数的图片是不足以让我们震惊的,不在现场的人,我们不谈日记,日记是一个见证,是文学见证,那么栗子的作品是一个艺术的见证,我强调这个见证的重要性,可是如果说只放两个视频,三个视频是不足以让我们震惊的,当你放几百个,为什么它叫《160分贝》呢?我告诉你们,人类的承受极限是160分贝,你超越了160,你的耳膜就会被整破,所以160分贝是人能够承受的极限。这么多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2020年的上半年的在武汉发生的,空无一人的街道,有狗的叫声,有人的在医院里面叫的声音等等,当所有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一种超过我们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的另外一个声音,这是对这一种消失的声音的一种保留。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作品意义,这么多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带来的是一种噪音,而真的这种噪音,它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做见证,以及影像本身的,它的价值就是,把影像变成声音,变成一种媒介,就是图像变成声音,那么多的手机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场景。当时有个场景很打动我们所有人,就是很多在殡仪馆里面,那些没人收拾的手机堆在殡仪馆里面,而这些人都已经不见了,已经消失了,就只有一堆手机在那里,那这些手机是没有可能在收集到信息的,它是一个被抛弃的,被抛弃的以及没有人的、死者的遗留物,所以在栗子的作品里,艺术就是为一个消失的东西,为这种会被人类加速遗忘的那一个我们震惊的世界所见证,尽管这个见证他最后体现为一个噪音,或者体现为一个不可展览,但她依然展览,他会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现场观众
米诺:谢谢夏老师,夏老师刚才在讲栗子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夏老师对栗子作品的了解的应该比我更深一些,因为我跟栗子是生活中很好的朋友,但是她的作品我没有更多这么深刻的去理解。
但我也在想,就是所谓的“正在发声”好像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放到这个项目里面似乎是不合适的,但我为什么要很固执的去选了栗子这件作品,其实我一直在想,因为疫情的发生,我们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了,而且就到目前为止已经三年,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我们个人层面,它的影响已经是巨大的了。

朱赫:我和夏老师是武大哲学系的,我们相对来说是因为在武汉生活,所以当时其实对武汉的很多这个状况还是肯定有所感触的。 今天我来的时候查阅资料,以往我们讲艺术的时候,表达一个人观点的时候,我们会讲“抗议艺术”,但今天我查的时候出来的词,查了好几页发现都是“抗击疫情的艺术”,也就是“抗疫艺术”,这其实就有一点点荒诞性。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要去表达一个抗议的观念,抗议也意味有一个问题意识,人要表达自己啊,要去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 “160分贝”这个名字确实很好,因为现实中我们接触不到这个声音,人自己能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你要实在喊到很大声,大概也就100分贝,普通我们也就是40分贝,但是“160分贝”我们其实会有文学性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是很低的,但是大家一起发出的声音,在观念上面,在一个文学性的这种想象力上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发出一种声音他可能会达到想象中的“160分贝”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名字起的非常好。
谈到抗议艺术最早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俄罗斯的一个艺术组合“vonia”,他们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联邦安全中心,也就是国家安全局,在他那个安全局对面有一座桥,但是那个桥是一个可以通行船的,所以船一通行的时候,那个桥就要升上来,然后这个艺术组合,他们在那座桥上画了一个50多米的一个男性的阳具,然后每次在这个桥升起的时候,这个阳具就要对着这个联邦安全中心,竖了起来。
然后俄罗斯还有很多很好行为艺术作品,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暴力小猫、帕夫伦斯基、库里克这几个艺术家和艺术组合。我觉得俄罗斯艺术家很好的诠释了艺术如何去介入政治,介入生活,但是诗人希尼也说过,从来没有见过诗歌阻止过哪怕一辆坦克。艺术也没有阻止过任何坦克,可能每个中国的艺术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愿意去用特别过激的方式来去表达自己,表达一个问题,因为可能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习惯。栗子这个作品《160分贝》,我就觉得其实从行为艺术上面来讲的话,跟政治有关系的极多,但是她用一种更诗意的,更浪漫的方式,跟大家产生一种共鸣。
我们有时候也要去思考,面对武汉的这种问题的时候,面对将要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也许记录就是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艺术我觉得有时候他会把许多东西都屏蔽掉,他会筛选掉所有我们极端的情绪和非理性的状态,它是更温柔可以触摸的,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力量。

段少锋:2019年的11月我是在武昌。2021年的时候,我们和朱青生老师做了一个系列性的论坛叫后疫情时代,就转了朋友圈,然后川美的王老师就批评我们,就说现在还在疫情中啊,怎么就后疫情了,我想人家说的挺对的,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只不过是20年下半年,或者是21年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事差不多半年多应该过去,但这三年时间的这种感觉大家都变得麻木了。
栗子这件作品,我觉得它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个无法展示的作品,今年和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在聊天,他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隐”的时代。
他说一个作品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有两面性,我们怎么去阐述一个作品。比如说栗子的作品,是不是我们拿到一个所谓在谈生生态问题,谈艺术与科技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变得非常合理了,他就是变成一个人与自然的问题,我觉得这当然是没问题,为什么不能展览呢?对你的解读层次非常多,很多90年代的作品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徐老师《天书》也有很多不层不同层次的解读。我觉得其实这种所谓的“隐”,所谓的双面性都是有的,这个作品真的可以展览的。
这两年关于这种所谓疫情时代的作品特别多,2020年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做艺术和疫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就俩事,一个抗疫艺术,一个慈善拍卖。因为艺术的反馈是后置的,他没那么快,我到底应不应该围绕一个这么一个话题去做一个作品,其实你这个作品只能今天发布,你当时发布会遭很多人嫌弃的,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不是在去思考一个艺术问题,而是这个你到底是不是在蹭热点,当时画钟南山的肖像、口罩什么的。
我刚才说我们的解读是多重的,你在不同的语境里头去谈一个自己你想谈的问题,我刚才想了好多种,我一直觉得我们聊的都挺沉重的,一旦谈到这三年,但是我觉得另外挺奇怪的一点,19年我做过一展览《玩笑》,你不能直接谈现在的问题的时候,你去谈另外的一个问题时候,我觉得九零后或者八零后的艺术家,对待现实问题变得越来越有一种自嘲,有点像是90年代的顽世现实主义了,我觉得那会儿是不是也有一种所谓的叫“躺平”呢?我觉得也有点躺平。我觉得现在躺平也很正常啊,那年轻人怎么去表达,就是你很多无力的时候,就这么着吧。
2020年的时候,大家过年的时候不停的刷手机,过年的晚上很焦虑,没有一个年是这么过的,这个事儿越往后走越有点不对劲,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喜感,就是你能明白吗?有种狂欢的感觉,这个事本来是个不是特别高兴的事儿,怎么最后就变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你这个视频也是没问题的,当时有一个蔡灿煌,是一个艺术家,是蔡国强的助手,他就把这个过年期间抖音的很多这种搞笑段子全部都下载,这事其实是个不好的事,但是为什么在这这里边又有一点喜感,就是这个感觉很莫名其妙的。就完全变成了自嘲。
栗子这个作品,我也想到两个作品,一个是就蔡灿煌,他是关于一种调侃。栗子这个关于痛苦。蔡国强也有一个关于狼的作品,是一群狼到一个独狼,刚好是一个从全球化到去全球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

(左)栗子、(中)米诺、(右)夏可君
栗子:这个作品在我所有作品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社会生活的人,我认为生活是很世俗的事情,我喜欢在作品里面表达崇高和永恒。所以《160分贝》是我所有作品里我认为是最特别的,我真的是想去找到一种冲出去的力量,然后我要去思考,冲出去可能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消失掉了,但是我也要冲出去,就是这么一个力量,一种狮子从一个黑暗里面冲出来的力量,然后这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装置作品。
米诺:为什么选择了栗子这件作品作为这个“正在发声”这个项目,第一个是勇气,再一个就是要给我们表达的权利。她的这个160分贝,其实很像一种呐喊,其实这个所谓的呐喊,她要把这个声音冲出去呢,一定是有反抗的东西,我觉得是存在的。

直播现场
朱赫:艺术家也可以作为一个编年史的学者,或者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记录者,用记录来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栗子作品里面其实就有这种力量,力量是深沉的,不是说我要去高高呐喊,说疫情不对,或者世界各国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是。我们一切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今天所有这事情发生到现在都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啊,如果我们需要沉默,那也要用记录的方式来去穿透所有无法言说的东西。
段少锋:恐惧的记忆可能是不会消除,现在只是种子是落下的,我想中国社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恐惧加郁闷,就因为常久的恐惧抑郁,就是我说从一种就是如是做,主要是政治郁闷症啊,中国有一种来自于恐惧的郁闷症,可能是未来在社会要化解的,如果说艺术它能够为这一种恐惧作为底色的郁闷提供某种表达,勇气表达和化解是好处,这是好事情,艺术他的药作为治理,作为作为一种药,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好的,不必要害怕,这艺术家的某种责任,在这个年代的,可以这么说,就叫更敏感,所以他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他分别那么强,他用那么大的力量就想冲出去,就想冲出这个恐惧做的囚笼。

《160分贝》局部
文章来源: 艺术家栗子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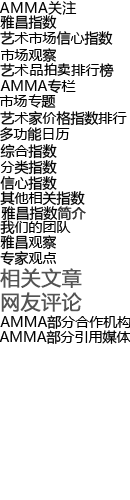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