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提到中国绘画史中最著名的作品,应该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然而,现如今家喻户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般被认为是张择端真迹的这本《清明上河图》(图1),北宋时却未入《宣和画谱》,我们也无法在其他同期文本中找到关于它和它的作者的只言片语。从这个角度上说,《清明上河图》在其初创时,很可能不甚重要,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件公认的名家名作。
那么,《清明上河图》在何时,又如何声名鹊起呢?
图1:《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绢本设色,24.8×528.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清明上河图》的声名鹊起,大约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文献中《清明上河图》出现的频度得以推知。相比早期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述,从明中期,大约嘉靖朝以后开始,涉及到《清明上河图》的文献爆发性的增长,而这种骤然而起的热度,一直持续到清末还未退却。
明清时代,许多生平并不一定与书画有涉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诗作中,却常能见到《清明上河图》相关的意象和典故。譬如朱茂昞(生卒年不详)《清明日过高梁桥》有“那得丹青寻好手,清明别写上河图”;赵翼(1727-1814)《湖上》有“堤上香车堤下舫,清明一幅上河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于清初官修教人写诗用韵的《佩文韵府》,谈及“图”字韵时,所举例子正是“上河图——画苑宋张择端有清明”。可见,明清时期,至少在知识阶层中,《清明上河图》是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更有趣的是,与一般名家名作往往只出现在严肃文本中不同,《清明上河图》在明清时代还常常出现在一些极为世俗化的语境里。譬如小说《金瓶梅》就与《清明上河图》扯上了关系。明清时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大致说《金瓶梅》实为王世贞(1526-1590)所著,王世贞之父王忬(1507-1560)曾献赝本《清明上河图》给严嵩(1480-1567)严世蕃(1513-1565)父子,因被唐荆川(1507-1560)揭发而生死,王世贞便著《金瓶梅》涂毒药其上,毒杀唐荆川为父报仇。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吴晗先生已经雄辩地证伪了。但是当红小说、权柄人物以及文坛领袖,《清明上河图》能与它们摆在一起,正说明它也如它们一样在明清时已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存在。小说《金瓶梅》以外,戏剧《一捧雪》和《焦山鼎》也与《清明上河图》有所牵扯,它们同样说明《清明上河图》在明清时人心目中的位置。
明中期以后开始至于清末《清明上河图》的热度让我们疑惑:一般认为创作于北宋时的《清明上河图》,为何流传至于明代中期以后才获得这样的声名?一般认为的张择端真迹,尽管在多位私人藏家手中流传和传承,但在没有公共展示平台和缺乏现代传媒的古代,能够目见它的人毕竟少数,那么明清时的人们又通过什么去认知《清明上河图》呢?
这便要从明中期以后,所谓真迹以外的另一类《清明上河图》说起。这类《清明上河图》无论是绘画风格还是画面内容都与所谓真迹存有明显的差异。它们通常为绢本大青绿设色,画卷开始处常见山峦,虹桥为石质,城门楼带有瓮城和水门,画卷结尾处往往可见所谓“金明池”的宫殿和龙舟。它们的画风近仇英(约1498-1552)一路,也多见仇英伪款。学界一般将它们视作是明代中期以后“苏州片”一类民间作坊生产的赝品和伪作。
需要明确的是,这类《清明上河图》数量非常惊人,童书业先生曾非常夸张地说:“可能以千万计”。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先生和古原宏伸先生都曾对现存此类《清明上河图》做过统计,但都未能穷尽。笔者曾做过调查,仅藏于全球各大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中的便已逾百幅,私人藏家手中的更不可胜计。现存的数量就如此惊人,可以想见在明清社会,它们会是怎么样的保有量。
惊人的数量使得这类《清明上河图》得以在明清社会中广泛传播。从明清时期的文献来看,许多著名的文士,其所藏或所见的《清明上河图》事实上都是此类。譬如,李日华曾于《味水轩日记》中兴致勃勃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万历四十二年(1614)两次得见的一本《清明上河图》应是张择端“真本”。然而从他描述的“沙柳远山”开端,及画卷有“赐钱贵妃”句,卷后又有苏舜举、戴表元、李冠等人跋文来看,这个本子应该是非常接近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明易简图》和东府同观本的版本,即也是这种明清时期生产的青绿设色的面目。(图5、6)
图5:《清明易简图》,(传)张择端,绢本设色,38×673.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图6:《清明上河图》(东府同观本),(传)张择端,绢本设色,39.7×60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从文献记载来看,沈德符(1578-1642)、钱谦益(1582-1664)、彭孙贻(1615-1673)、查慎行(1650-1727)、吴荣光(1773-1843)、裴景福(1854-1924)等人收藏、目见,并记录下来的《清明上河图》,其实也都如此。甚至如邵圭洁(1510-1563)、张凤翼(1527-1613)、王士祯(1634-1711)、翁方纲(1733-1818)等人还都至少见过两本以上。
虽然按照目前学界的看法,这类《清明上河图》的生产基地应是以苏州为中心,然而这却并不妨碍这类图画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苏州、北京、南京等等当时的文化中心城市自不必说,明代王象晋(1561-1653)有一篇《张襄宪公远虑传》,记载说哪怕在偏远的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县)也曾有过一本《清明上河图》。此外,赵荣祏(1686-1761)《观我斋稿》、朴趾源(1737-1805)《燕岩集》、伊藤东涯(1670-1736)《绍述先生文集》、斋藤谦(1797-1865)《拙堂文话》等等日韩文献中的记载还佐证,这一类《清明上河图》在17、18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
如果系统考察和比对便会发现,明清时期生产的这些《清明上河图》,它的广泛传播,与《清明上河图》知名度的发展是共时的。真迹当然也在流传,然而相形之下,这种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图画,才是明清时人真正能够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图像,是他们能够直观认知到的《清明上河图》。当这类《清明上河图》投向市场,进而进入到收藏和赏鉴体系中,必然地,人们需要一整套关于它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大量讲述它的文本、生成了大量相关它的知识,甚至还演绎出关于它的传奇。当然这些文本、知识和传奇,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图像的生产和传播。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关系。
一般认为的真迹,艺术成就固然高妙,然而在没有公共展示平台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古代,它的影响力是局限的。而那些现如今被斥为赝品、伪作,一般认为艺术水平不及真迹的图画,却好像今天的印刷品一样,以其惊人的传播力作用于当时人的认知。在当时许多人那里,那就是《清明上河图》的样子。图像伴随知识,如今并不受到重视的所谓赝品和伪作,恰恰代替真身早早于明中期以后便成就了《清明上河图》的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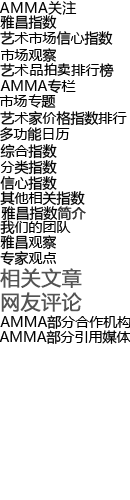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