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首先感谢红梅老师和孙志义老师的诚挚邀请!
再次回到中国油画院云上博物馆现场,特别感动。因为云上博物馆不是我个人的设计作品,而是集体创作意志的成果。就像此时此刻《板象》展览所呈现的令人震撼的精神性,至少是三个主体、三种念力精长期累积、持续集聚、相互支撑的结果。
第一,此时此刻的现场是大艺术家与教育家杨飞云先生10年意念与意力的结果。杨飞云先生从最初的选址,到早期的发愿,到中期的波折,到最后的完成,投入了巨大的信力、心力与念力。正是这些信力、心力与念力使得这个空间得以最终显形,得以以这样壮观的、浑厚的、吸纳的力量,与我们今天相遇,也引发了我的层层回忆。我甚至能重新感受到,与杨飞云先生、油画院的诸多先生以及工程师们的方案讨论,还在这个空间的不同位置回响。
第二,此时此刻的现场是策展人红梅老师2次云上博物馆策展事件以及3年深度个案研究的结果。红梅老师不但发掘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更是以敏感的问题意识、近距离的个案深描、系统化的档案梳理、空间化的情境营造、综合性的场所感知、场域化的策展实践,给我们呈现了当代策展实践独具的思想力、批判力、洞穿力与粘合力。正是这个策展才让这个空间内嵌的秩序性、包裹性、身体性被被一一唤起,被层层打开,让我第一次震惊性的看到一个策展实践所能赋予建筑空间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此时此刻的现场是艺术修行者王绮彪老师10年潜心劳动与创作实验的回响。之所以用“劳动”这个概念,是因为每件作品中都蕴含着极大的能量,都是王绮彪老师一次次探索仪式的见证与物化。之所以用“创作”这个赞叹,是因为在当代艺术语言日益枯竭的时代,这些作品令人惊讶地探索出了一种超越传统版画语言的新世界,并把对于当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批判,成熟且不露痕迹的内嵌其中。
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时此刻这个展览,也许可被理解为多个精神主体与精神实践者的跨时空对话。他们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一种原初的可能性转化为潜在性,而潜在性又转化为现实性,现实性又再次转化为一种可能性。这些持续的转化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呼唤,是一种能量对另外一种能量的呼唤,是一种实践对另外一种实践的呼唤,是一种设计对另外一种设计的呼唤。因此,油画院云上博物馆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建筑设计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念如何变为建筑设计、策展实践、艺术实验的故事。或者说,一种信念,经过10年时间,将所有的主体、能量、实践,逐渐汇聚于此,成为了一种形式。为了揭示这种形式的内在历史与机制,我将选择“设计”、“策展”、“创作”三个动词,讲三个有关这个展览的故事,就像红梅老师为王绮彪老师编纂那个手册那样,解释它们如何穿越种种“不定”,最终达到一种“笃定”。
设计
最早和杨飞云老师商量建筑概念的时候,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本质是一个“精神工厂”:工厂是它的结构,精神是它的内核,博物馆与美术馆就是在结构性工厂空间中所发生的所有精神关系的总和。正是这个观点支撑了这个建筑4个关键环节的始终:一是理论认识,二是观念生成,三是设计导则,四是精神场景。
从理论认识角度看,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本质是工厂,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交换的场所,这是因为博物馆与美术馆要用一个稳定的结构,承载所有变动之物,承载所有变动之态,承载所有变动之事。但是,博物馆与美术馆不能替代最终的形象,不能规定最终的形式,不能计划所有的内容,只能成为一个中性背景。无论怎样,作为物的建筑,都只能回到它的中性身份,只能克制的成为精神的载体,而不能直接代替精神本身。建筑之美正在于克制之美。这个中性背景可以有必要的空间倾向,但必须克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为只有在这个中性背景中,所有可能的意向才得以发生,所有可能的内容才得以生产,所有关于可能性的可能性,才能得以酣畅淋漓的生成。只有连续不断的生成,才能使得信念与现实之间反复生成,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精神意向。
从观念生成角度看,何种中性化的建筑语言,才能表达一个承载无数信力的精神工厂?答案是:一个具有洞穴意向的当代空间,其意向理路是:人类最早的空间场所,不是由标准化柱网搭建的巢穴,而是迷宫式的洞穴。洞穴是人类的空间性起源,甚至最早的狩猎场景的岩画,也是在这种洞穴空间中被发现的。洞穴代表了一种与深度安全感有关的人类内在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图像、仪式、生活,甚至帕拉图的关于影子的理念,逐渐孕育出来。我想,要使得当代的工厂成为一种精神工厂,那么,它的空间气质就必须具备洞穴性的特征,但是,我们又不能用传统洞穴式的建造方式,我们只能通过当代经济化的柱网建造方式,获得洞穴的意象,才能承载深嵌于人类文明之中的精神性内涵。
从设计导则角度看,如何从当前局限性的现实建造条件中批判性超越出来,就是设计导则形成的核心。当前最为经济的建筑结构技术,是方格形柱网,这是最普遍的表达,也是最没有特色的表达,它是对现代性抽象化、标准化、经济性逻辑的直接反应,也是浅薄化的反应。今天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空间都无法脱离柱网结构,但这种空间在获得现代性本质的同时,却把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精神性去除的干干净净。如何以这种现实约束条件为前提建设一个精神工厂?最终的两个建筑解决思路是:一方面,把一个标准化8米柱网中的每一个柱子,变成一个1.5米×1.5米的空间,使之成为由4个L型墙体形成的微型身体化的洞穴。这样,以这样的洞穴作为基本结构单元,就可以支撑起来这个建筑所需要的所有空间。另一方把这个洞穴结构体旋转45度,向四个方向蔓延,使得建筑空间成为一个内向性的迷宫。正是通过洞穴与迷宫的结合,这个建筑找到了批判现代性标准化技术,以及向早期文化起源的现代性致敬方式,并逐渐接近了精神工厂的本质。
从精神场景角度看,仅仅建筑本身的完成,并不是真正的完成,因为它还缺少一次真正的精神性艺术事件。真正使建筑具有精神性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具有精神力量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它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好的建筑不是局限在表现自身,而是要为思想的生成与出现留下必要的空白,建筑就是建造空白的艺术。正是这些空白,在呼唤一次特定情境、一次文化策展、一次艺术事件。这就是这个建筑如此需要这次策展以及这次个展的原因。
策展
策展是一种成象实践。从洞穴意向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中,一种“象”的意识逐渐复苏起来。突然发现,“象”的思考,已经在红梅老师这次策展理念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表达。于是接下来,我想从设计者的身份中退场,作为一名学习者,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不是从立面,而是从剖面,以红梅老师的“板象”理念作为“核心理念”与“思辨路径”,聚焦策展创作与艺术创作的方法论,打开“板象”思想之中三个环环相扣的命名层次与方法策略。一方面,我尝试解读:红梅老师为什么以这个概念命名?另一方面,我尝试解读:王绮彪老师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创作?基于这两个任务的反复推进,我将展示一些学习心得,打开一些潜在对话,并向策展人与艺术家致敬。
用一句话阐释红梅“板象”的策展理念就是:“木之反象,由反成象”。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曰木,二月反,三曰象。“木”、“反”、“象”并非三个孤立的层次,而是潜在的构成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策展逻辑。
红梅的第一个策展逻辑是“木”。在策展前言中,红梅老师通过“板”字,而不是“版”字,明确清晰的告诉我们,王绮彪长达10年的创作材料与总体主题,就是“木板”,不是“版画”。这里的“木”,不是“自然之木”,不是“原生态之木”,而是“工业之木”。红梅在策展理念中清晰地指出,工业五合板就是王绮彪的艺术工地,就是创作材料,就是物质性本质。工业五合板的生产性本质是,原生态的自然之木,被工业钻刀一层层切割,之后经过高温蒸馏与压缩,去除了所有自然之木的生命力,成为了一个1.2米×2.4米的标准工业之物。在红梅看来,王绮彪的创作逻辑,就是面对工业之物,一种死亡之物,给它“反”回去,重回一种生命性,重回一种精神性,重回一种气象性。也就是说,“五合板”,作为一种抽干了生命的工业之物,只有经过一个复杂的精神性操作、身体性操作、艺术性操作、逆向性操作、否定性操作,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新生,升华为一种美学之物,一种“大象”之物。
红梅的第二个策展理念是“反”。“反”在这里不是简单的反面,而是一种对工业之木的反观,一种时间性的反回,一种文化性的反思,由此揭示深刻的矛盾性,投射批判性的激情。反思,意味着重新思考版画从复数性到单数性的历史性逆回,这是一种文化之反。矛盾,意味着只能通过直面工业材料本身的无生命性,才能重新回工业材料的生命性,这是一种方法之反。批判,则是对已经彻底物化的工业社会的当代艺术批判,这是一种价值之反。红梅老师坚持对王绮彪展开三年个案考察,就是想进入艺术家创作之初所面对的矛盾情境,以及艺术家创作主题所针对的批判之物。所以,在策展安排上,红梅不想直接呈现王绮彪的工作结果,而是在展览最先开始的地方,呈现王绮彪近10年来的创作日志,它们安静的在拱廊通道中向观者们低语。红梅将这些创作日志精心的编排,将其中内在的矛盾性张力呈现在展览最先开始的内容,由此揭开了一个艺术家无法回避的成长经验、叙事性伤痛、阶段性犹豫以及特定时刻的爆发。只有返回时间的原初以及动机的起点,才能重新开启对于已经死亡的工业之木的复活仪式。
红梅的第三个策展理念是“象”。“象”在这里不是指木板的气象,而是批判的气象,是“由反成象”。“由反成象”就是说,只有“反”,才能“成象”,只有“反”,才是真正的批判,只有通过真正的批判,才能够成为形式(不是形状,而是形式)。形式分两种,一方面成为“形”(精神之力凝聚成形的具体性),一方面成为“式”(方法性与语法性)。只有同时成为“形”与“式”,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形式”,一种持续的“生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开放式实践,才能生成真正的气象。为了辩证性表达气象的多元性和一元性,红梅针对王绮彪的每个独立作品所具有的批判性能量,在建筑空间的不同场景中进行了立体化、综合化、戏剧化的排演与布局。在这个意义上,王绮彪的艺术作品也成为了红梅的策展作品。她要仔细的体察每个作品在空间中与已有建筑秩序对抗的潜力:或者,让作品安静的内嵌在建筑空间的秩序序列之中;或者,让作品本身的抵抗性能量与建筑空间的秩序性能量直接对抗;或者,让某个作品位于多个空间轴线的交点;或者,让作品中深沉的黑色能量减缓行走旁边的观者的步率;或者,让作品在空间中高低不同的空间势位,俯视、平视或仰视观者;或者,让作品与作品之间形成大小、疏密、松紧关系的内部对话。通过这些布展策略,总体作品形成了一个既自主又开放的世界,它们与已有建筑空间不断发生平行、交错、纷争、或震荡的关系。在某些时刻,一种力量与另外一种力量相互对冲,在另外一些时刻,一种力量与另外一种力量又相互缠绕。正是通过策展,这些作品形成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总体气象。
创作
如果说“板象”命名蕴含的“木”、“反”“象”三者,形成了策展人红梅的内在逻辑,那么,在艺术家王绮彪的创作那里,“木”、“反”“象”三个层次,又是怎样逻辑性呈现的呢?比如,他的“木”,除了可见的工业之物属性外,还有其他特殊之处吗?他的“反”,有几种策略与方法呢?他的“象”,又有何种独特个人经验呢?
回应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要进入艺术家的内在方法世界,才能揭示艺术语言本体的价值。因为就像蔡国强所说的,艺术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艺术本身来解释,但艺术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艺术语言本身来解释。仔细的考察后发现,王绮彪的艺术语言,最后都凝聚在三种不同的“反”的策略之中。只有深刻解读王绮彪三种“反”的策略性——反“工业之数”、反“虚假深度”、反“表面色象”,我们才能理解王绮彪的艺术语言的批判性立场、独特方法与价值贡献。让我们尝试逐一打开:
第一种批判,是反“工业之数”。工业本质是数量问题,是自然的标准化。标准化意味着质的差异性,最终被数的同一性所取代。自然界中没有相同的物,工业却是同质物的大规模复制与累积。大规模复制之物与累积之物只有数量,没有本质。因此,对于五合板这种工业材料,批判的要点是:不但要反抗工业之物的“质料”属性,更要反抗工业之物的“数量”属性。这正是我们在细读王绮彪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首先,王绮彪保留了工业化五合板的生产编号之数。这是一种潜在的、冷静的、内嵌其中的生产主义批判。这些生产编号是被工业油墨所标定的合格证,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它们是自然尸体的沉积岩。其次,王绮彪没有停留在这个工业产品标签的表面化数字阶段,而是进入到了工业化模数制度批判阶段(1220mm×2440mm)。作为早期受过建筑教育背景的王绮彪,他不难发现所有工业之物都具有一个标准化模数性的属性,因此,他必须让自己的作品本身,也成为这个标准化模数体系的一部分,才能在原理上揭示五合板工业材料的标准化模数化本质。因为他的所有作品都内含了一个基准工业模数,所以,他的作品系列中,既有小作品,也有大作品,小作品是大作品的模数,大作品是小作品模数的倍数。大作品因为内嵌了“数”的概念,所以把中国文化中的“象·数”逻辑辩证地连接在了一起,小作品正是因为成为了大作品的模数,因此随时具有被吸纳到一个更大作品中的层级转型,使得作品的体量性具备无限扩张的可能。最后,工业模数语言的介入使得艺术语言出现了突变,引发了突变性创新的可能。正因为它是模块化的木料,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一个白色或黑色油墨,突然在某处惊险的停止了,那个地方就是工业板材的机器切割之处。这种暴力性的断裂,在传统版画是不可能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在油画创作能有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一个完整的边界之内,构思呈现下一层级的完整,它们在追求完整的过程中,谋杀了断裂能量的可能。正是因为王绮彪作品内部充满模数的存在,所以作品内部总是充满了断裂的撕裂与中断。这是一种极具张力的断裂原因,因为他把工业生产领域的断裂性能量吸纳其中。这就是王绮彪的“工业模数”之反。
第二种批判,是反“虚假深度”。王绮彪对于深度的理解不是幻觉性的深度(就像在油画中看到的),而是物质性深度;不是虚假深度,而是真实深度;不是间接再现,而是直接呈现。就像我们在红梅老师文章和发言中看到的,王绮彪这批作品的迷人之处,就是工业五合板物质技术构造深度的真实深度表达。他的表达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不是保留,而是刻除。对王绮彪而言,当他把日本的小型雕刻刀换成大型雕塑刀之后,身体性的能量在那一刻就被唤醒。他的工作就是把五合板的五个物料层级,真实性的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是一种对伤痛的揭示,因为每一刀下去,五合板的五个剖面层次与材料就被卷入一种暴力撕裂与坚硬拉扯的沟壑伤痛之中,无一幸免。细读这些沟壑的起伏,往往触发某种身体反应,甚至产生以下体验:每一刀似乎不是面向五合板,而是面向自我身体的真实性。这是一种阿多诺所说的否定美学方式。艺术只有在揭示伤痛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艺术之美不是在掩盖伤痛,而是是在揭示伤痛。艺术的深度在于揭示伤痛的深度,不在于掩盖伤痛的深度。揭示伤痛的深度就是接受伤痛内在的矛盾性,一种艺术越是能够揭示内在的矛盾性,这种艺术才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批判。如此,王绮彪的创作实践就变成了一种否定性创作。在这里,否定性既是工具,也是目的。否定性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不是面向木板,而是面向艺术家自身。刻刀在五合板上的划痕与刀痕,就是刻刀在艺术家身体上的划痕与刀痕。甚至每一刀都是自我身体与木板身体的激进战争,最终的作品仅仅是这个战争临时性的调停,一个惊心动魄的战后现场,以至于观者不得不被巨大的战争能量所吸纳其中,就像一种萨满教仪式的投影。投影不是我们面向过去,而是过去面向我们投来。也许今天艺术的一个批判价值就是重新回到原初文化中的那种原始能量性,一种自然之物、工业之物、身体之物无法分离的浑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王绮彪的创作最终是一种关于否定强度的创作,而不是一种仅仅局限在艺术语言内部的关于肯定性的艺术。
第三种批判,是反“表面色象”。王绮彪艺术作品中的否定性不仅仅停留在工业五合木板的数量、层次两个维度,还存在于木板颜色维度。首先,王绮彪的作品不是主观赋彩的产物,而是墨色与木色发生战争的地方。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创作策略,是因为王绮彪所选用的作品本身是现成品,而现成品已经内嵌了工业之木原初的颜色,因此,他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现代性底色的工地。他是在已经存在底色的工地上,继续“投射”自己的心象色彩,这些心象色彩是一种浓淡干湿不断变化的黑色油墨的痕迹,这种投射可被理解为一种笔刷在工地上纵横驰骋的系列战争。因此我们看到的作品色彩,是战争之后的产物,是一种黑色油墨对原本工业暮色覆盖之后的产物,而不是提前规划好的直接性表达。其次,王绮彪的作品不是加法性的、塑造性色彩的产物,而是减法性的、拆毁性色彩的产物。加法性色彩与塑造性色彩更加接近传统的油画创作与实践,是无中生有的过程,是人的主观艺术投射在画面上的结果,例如,塑造物象的结构,塑造物象的肌理。与之不同,减法性色彩与拆毁性色彩则更加接近王绮彪这一批创作的色彩生产逻辑,是有中生无的过程,是黑色与白色两种否定性的、覆盖性的材料,在已然有底色的工业木板之上,持续正向、反向覆盖的过程。有时是黑色对木色的覆盖,有时是白色对木色的覆盖,有时是新一层黑色对已有黑色的再覆盖,有时是新一层白色对已有白色的再覆盖,有时是黑色与白色的相互交织覆盖。在形成最终作品色彩的结果之前,王绮彪始终处于一种激烈行动状态之中,他无法准确预判最终色彩分布,甚至无法准确控制油墨与木色之间的能量流动,他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何时暂停,或决定何时继续。最终作品所呈现的色彩,是临时性调停的结果:在那些黑色与白色透出来的工业木色,突然变成了一道道光线,刺破了覆盖在它们身上的黑色油墨,成为一种精神色彩,成为一种精神气象。王绮彪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这些矛盾的对冲性的力量,在已有的工业木板褶皱中来回震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王其彪的作品色彩不是加法色彩,而是持续相互覆盖、破坏所形成的减法性色彩、拆毁性色彩。油墨不是画上去的,而是覆盖上去的。这种覆盖不是一种塑造,而是一种破坏。通过拆毁性的覆盖过程,让我看到了工业化的残酷一面,像柏油马路对自然的覆盖,是对自然土地的破坏性覆盖。当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的时候,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通过对工业之木原有色彩的破坏,才能够让原有的工业之木的原色成为色彩。只有用油墨去覆盖木色的时候,木色才得以浮现。只有用油墨去覆盖木纹的时候,木纹才得以浮现。只有用油墨去覆盖木面的时候,木面中的伤疤才被凸显。没有破坏过程,我们在工业木色的表象之中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王其彪的作品色彩仍然保持着版画媒介的拓印性。拓印是一种印痕之美。正是在印痕的角度上,我看到了木板作品与建筑墙体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它们是两种十分接近的印痕。建筑中的柱子是混凝土模板浇注之后的产物,而这些模板是由工业五合板制造完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工业五合板在被拆毁之前,已经深深地将自身的微观肌理,刻写在了混凝土的表层肌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空间中展示王绮彪的作品,总有一种说不出来、但的确存在的内在气韵的流动性。因为,建筑之物与作品之物,它们都是印痕之物。
王绮彪作品的气象,就是在这三种“反”的策略中诞生的。一是反(工业)木之数,二是(工业)木之层,三是反(工业)木之色。然后反之又反,就形成了作品的最终气象。三种“反”如此辩证的整合在一起,相互地嵌套,相互地综合,负负得正,反之再反,最终形成了具有结构主义力量的生成方法论。一旦一个作品不自觉地使用了结构主义生成方法进行创作,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力量就回支撑这个作品内在的不断的演化,就会推动这个作品必然从单个作品形成一个系列作品。虽然每一个作品是独立的,但因为所有作品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主义方法论的逻辑下进行的无数的探索,那么,由此形成的系列作品也就回答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与多的问题。只有回到一和多的逻辑,才是象的本质逻辑,才是象的原初逻辑,才是大象无形,才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才是恍兮惚兮,其中有数,才是象外之象,才是无极。我觉得,红梅老师的这个命名,真的是非常完整深刻地概括了王绮彪创作的方法论,也概括了建筑最早设计的时候没有实现但希望实现一个方向。
再次感谢杨飞云先生,感谢红梅老师,感谢王绮彪老师,让建筑有了精神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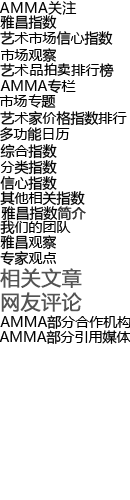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