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01
艺 林 藻 鉴

陈仕彬
书画家
中国画题款中“写意”与“制作”漫谈文 | 陈仕彬刊于《艺术市场》2022年4月号
在当今物欲横流、制作之气横行的时代,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严重缺失,书画家应该养心、养浩然之气,努力提高自己的涵养与修为。
一幅完整的中国画,通常由绘画、题款、印章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浑然一体,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审美系统。题款源于款识,原本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对浇铸这一器皿缘由的说明,后沿用为对书画作品作者及内容的说明。在当今的画展,尤其是在全国美展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大尺幅、工艺精良的作品,题款为“某某制”。除展览之外,一些画家在日常创作中也以“制作”二字进行题款,如齐白石。诚然,工笔或者兼工带写的作品,题款使用“制作”二字无可厚非,但在写意作品上使用“某某制”进行题款,似乎有失妥当。
“制作”侧重规则、标准“制作”一词具有制造、造作之意,也可指礼乐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史记·礼书》:“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今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东周列国志》第四回:“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礼乐吾祖之所制作,子孙用之何伤?况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鲁?’遂僭用郊禘,比于王室。”《说文解字》中说:“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一曰止也。”含义为依照规定的标准做。由此可见,“制作”一词,侧重规则、标准,总体而言是皇权贵族和民间百姓所强调的工艺概念。从社会阶层来看,民间百姓是劳动的主体,皇权贵族则是享受劳动成果的主体,二者对“制作”有着共同的认知概念。从而,为这两个阶层服务的宫廷画与民间职业画,有着严格的标准、规范。然而在唐末宋初,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崩塌,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快速上升,成为新兴阶层,且占据社会重要地位。为了强调自己“文化英雄”的社会地位,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有意与宫廷画、民间职业画拉开距离,尽可能地摆脱规则的禁锢,追求自由,书画为寄。如赵孟頫问钱选:“何以称士气?”钱选明确回答:“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由此可见,文人画经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理论先行,到元代达到高峰,明确反对“匠气”,而追求自由抒发性情。这一切体现在款识上,则是以“写”“泻”代替“制、作、画”,甚至在现当代也有很多艺术家以“一挥而就”作题款,齐白石常在作品上题“白石一挥”。
实际上,“写”“泻”“挥”集中体现了文人写意画的理论追求,分别是:写--以书入画、泻--直抒胸臆、挥--恣意挥洒。

写--以书入画以书入画是文人画区别于职业画的重要特征。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述“书画同笔”的问题时,是从中国汉字六义中“象形”这一法则与绘画的关系入手。陆探微的一笔画借鉴王献之的一笔书,“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僧繇用笔“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石涛《题画诗跋与题记》中“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莽莽率天真,不然试问张颠老,能处何观舞剑人”,更是生动地描绘了书法和绘画的关系及情境。因此,张彦远认为“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郭熙同样认为作画用笔,可以“近取诸书法”“王右军喜鹅,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转腕以结字,此正与论画用笔同。故世之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在此基础上,赵孟頫为文人画的用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应当“书画同源,以书入画”。
泻--直抒胸臆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文人画用笔理论,客观上也促进了绘画功能从“成教化、助人伦”等的实用功能向抒情言志进行转移。中国早期的理论,强调绘画的实用功能,绘画是视觉艺术,可以记录客观形象。甚至按照王充的看法,与古之遗文相比,图画似乎没有什么存在价值,只能对目不识丁的小民才有一点震慑作用。总之,早期的画论专著中,一直强调的是绘画的政教功能。然而,书法则不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便已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进行看待。书法的意义不在于有记录之功用,而是能够“书意”。王羲之云:“夫欲书者……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震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落笔之前,先成意象,于是,书法也就有了抒情的审美功能。书法的抒情功能,随着以书入画,也成为文人画的自觉追求,正如黄庭坚《题子瞻枯木》所说:“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作画不为盈利,不为取悦统治阶级,只为表达强烈的情感,正是文人画不同于职业画的重要特征。文人作画的过程亦是倾泻强烈情感的过程,恰如郑板桥所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挥--恣意挥洒北宋以前,绘画表现的细与慢,一直以来被推崇--慢代表创作态度的认真,细则表示绘画技法的精纯;而快代表在前两者基础上激情的注入。文人画的功能是抒发自我的情感,情感的稍纵即逝决定了文人画不能像职业画那样精工细作。苏轼以文同画竹来说明,经过苦心孤诣或者审美意象成竹在胸之后,便是运笔急起直追,快速无间断地将心中意象呈现于纸上,以“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的比喻来强调创作快速的重要性。这从用笔上最终导致了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艺术追求。这种挥洒的恣意性,说明文人画家是以一种游戏的创作态度即兴挥毫,抒发当下的意兴。自北宋“二米”的“云山墨戏”之后,文人画家标榜作画时“聊以自娱”的业余创作态度。这种创作主体的游戏态度,在宋代的文人画家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北宋著名的诗僧、画僧惠洪将禅宗思想运用到文艺创作与品评中,主张“在欲行禅”“游戏三昧”。苏轼画应身弥勒像时,惠洪赞叹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其与“苏黄”等士大夫交游甚密,从而推动了“以笔墨做佛事”“游戏翰墨”的书画理念的传播与盛行。苏轼在《题文与可竹》中说:“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他指出文同画竹便是以游戏的态度出之,而入竹之三昧。这种游戏、任意的创作态度是文人画不同于职业画的第三大特点,元代吴镇有言:“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

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局部)
逸笔草草的性情表达总体来说,“制作”一词,多指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与文人追求自娱、随兴、抒情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相去甚远。“制作”包含了极强的实用和功利性,而“写、泻、挥”则体现了文人士大夫逸笔草草、直抒胸臆的性情表达。同时,精工细作的“制作”所需要的精力旺盛、视力良好,要在年轻时体力充沛的情况下方能进行。历史上,《清明上河图》(张择端于16岁到39岁之间创作)、《千里江山图》(王希孟于18岁创作)、《溪山行旅图》(范宽于盛年时创作)皆是如此。而当年岁渐长、视力昏花、体力衰退时,人生经历丰富而灿烂,无论是顺意还是失意,无论是郁结的块垒还是快意的豪情,都需要直抒胸臆、兴之所至。古今很多伟大作品皆是如此,如三大行书、四大草书及众多名画。此外,笔墨本身又有着向写意方向发展的自然属性,所以才有“天心月满、人书俱老”一说。在当今物欲横流、制作之气横行的时代,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严重缺失,书画家应该养心、养浩然之气,努力提高自己的涵养与修为,找回中国画写意的本心和正脉。
编辑|屈婷
排版|唐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 荐 阅 读

▲艺术&战争:悲剧的力量

▲林木:山就在那里--谈张大千艺术

▲丘新巧:书法作为一个学科来说还不完善 | 书法学科聚焦⑧

▲啸卷风云:吴昌硕画虎|朱万章
转自: 艺术市场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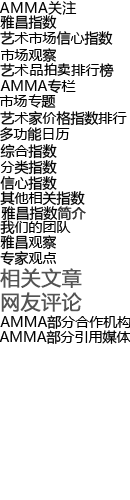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